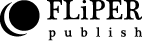【創作理念】
想寫一本,彷彿給「船上的人」拍特寫,那樣的詩集。
「船仔人」這個詞,是有次在成功漁港出海調查,聽船長閒聊時說到的討海人自稱。我深深喜歡這名字,彷彿他們與船共生,活在海上。後來我慢慢認識到,世上還有很多「船仔人」:重型帆船船長、賞鯨船船員、獨木舟教練、海上解說員······他們以船維生、活在海邊,或用自己生活所有的餘裕,喜愛海洋。
有沒有能以文字,記述他們日常生活刻痕的作品?接觸海洋的幾年裡,陸續搜羅與海有關的台灣書籍;小說散文有廖鴻基、夏曼·藍波安兩大作家,攝影集有李阿明《這裡沒有神》、簡信昌《1139km》,而詩集呢?我希望能自己寫出一本。
這本《船仔人》包括三個章節。「豬吃狗睡毛蟹走」取自賞鯨船長分享的閩南諺語,形容船員們工作匆忙、生活空間窄仄,主題記述在賞鯨港口的見聞,和我所見的海洋管理現況。「遺忘港」關於環島期間遇見的,幾個彷彿被擱置在城鎮更新、國際化、觀光慢遊等趨力以外,或者相反地,被無聲捲入的港口。「防風林裡的碎浪」是自己在花蓮海邊獨木舟基地的日常感觸;它們總與海相關。
出版的海洋詩集將佐以平日自己在花蓮海上,以及環島途中拍攝的照片。是海、岸與船的攝影集,也是關於海人們的寫生。寫不同背景的「船仔人」們如何活躍,寫他們的困頓和憂傷,還有在每個地方都相似的,海與岸對他們永恆的曠達與容納。
【《船仔人》詩集內容摘錄】
一、豬吃狗睡毛蟹走
〈可能加入了「船仔人」的那一刻〉
船長把自己抽到一半的煙
遞給你的時候
〈沒有名字的大哥〉
每艘船總有這麼一個船員
靜靜下樓抽油 掃地 清理救生衣
提醒你不用講他的名字
然後隱沒在下一班船的廣播裡
〈不是故意的〉
石喬假土魠
漂流木假背鰭
漁繩旗幟假海豚
浪花假豚游
遊客假船長
解說員假導遊
繞圈假遠航
海禁假親海
鹽和風浪
是真的
〈尾牙〉
每年有這麼一個晚上
所有人要一起坐著
吃完一頓飯
簽到的同時
瞭望幾張桌子像搜尋海面
確認同伴
和死對頭的位置
團康遊戲和抽獎
比往年都更加熱情
像不出聲地抓住大家袖子
我們不在同一條船上
但擠在同一個港灣裡
沿桌敬酒,貼上肩膀和腰的
是一隻手還是魚鉤
端看風向和水溫
碰撞過的故事都記得
只是喝得臉太紅,不好提起
順風逆流,陣陣白頭浪
風一平就成為歷史
仍在原地浮湧的海顯得蒼涼
主角們都還在
人群像同極的磁鐵
靜靜將他們推向
不再碰面的兩端
遠處港口遞來
無人察覺的汽笛聲
月亮攀爬到
比餐廳屋頂更低的冬季
此刻被晾在海上
無人聞問
〈鏢〉
牠(飛旋海豚)的身上還插有三叉魚槍,皮開肉綻……雖然解說員與人合力將牠救起,但傷勢實在太重,還沒靠岸就斷氣了。
——2016.06.09,公視晚間新聞
他們知道。
三支僭越命運的金屬箭頭
探入頸椎,穿過右肺
在打磨過的木條上蔓生鐵絲
向岸上無法滿足的慾望綿延
一支鏢旗魚的槍
埋進這隻飛旋海豚的身體
牠的靈魂沒有進港
到最後也不被捕獲
海風摻著實話刺進耳朵
一支鏢旗魚的三頭鏢槍
已經埋進船上人們背心的縫線裡
一頭倒鉤責任理念,一頭絞緊人情事理
剩下一頭在海面上碎成北風
船開過去
漣漪消散
他們當然知道
就像他們認得這片海域
每一道細小的浪花
他們認識每一個會鏢的人
彼此是兄弟,親戚
同村或隔壁鄉
至少是在海上遠遠見到
會在風裡揮手問候的朋友
有私怨才有罪行
他們緘默 像濺上船頭
逐漸乾涸的浪花
日頭在身上曬
篩出幾句呢喃像細鹽
在三樓甲板講的
在三樓甲板散
麥克風不廣播
我們帶回家的是鹽粒
鹹鹹的 稱不上眼淚
甚至不好下飯
我們慢慢知道
知道什麼可以說
什麼無法大聲嚷嚷
什麼事在脫力吶喊之後
像海沙般沈寂
知道大海的那一邊就是未來
但也只能慢慢航行
寫完這幾句就好
我會繼續學著知道
像在解剖台上
人們圍觀的目光中
一把刀子剝下表皮與鯨脂
切開肋骨
盤點器官與內臟:
食道,氣管,四個各有名字的胃
肛門(寄生蟲),生殖裂,睪丸,陰莖
微血管網,左肺與右肺
一顆與人類大小相近的心
順著鏢槍彈道的金屬紋理
沿血管上溯
我們將抵達一個如此飢渴的源頭
貧困,置產,原始狩獵的本能
抑或人生已沒有別的願望
海中的芭蕾舞者上了岸
擱淺磁磚平台,最後一次
在幾雙塑膠手套中轉身一圈
卸下血肉和骨骼
化為稍縱即逝
血淋淋的知識
呼吸是為了等待和徒勞和
再次期待
等這一代的寒夜過去
再等過下一代
等著有一天
我們和他們知道的
人們也終將知道
今日語焉不詳的句子
有一天可以拿著麥克風
跟船上的孩子們講:
「人們犯過錯
並在一代代的掙扎與傳述中
慢慢知道……」
〈關於海裡要沒魚了這問題〉
定置漁場表示
流刺網對海洋生態傷害很大
流刺網船長表示
定置漁網放那麼長
魚都被他們抓走
南方澳億元規模捕鯖船隊表示
是被海豚吃光了
旁邊小漁船說
「三腳虎」船隊鯨吞數千噸鯖魚
熱情的市民說
漁民都是愚民要負責
市場魚販說
民眾想吃什麼我們就賣什麼
學者和NGO訴求
保護區禁漁做海洋銀行
地方政府和民代訴求
不要影響漁業生計(和選票)
海裡生物訴求移民
到一個沒有人類的地方
〈柑仔色的〉
「柑仔色的來了沒?」
船長這樣張望著
船隻等待
一台臨時架好的鏡頭
一支對講機
兩個沒有名字的橘色衛兵
志願役 替代役
海洋或海岸巡防總局
不同臉孔 同一套服裝
我們習慣在碼頭
或用麥克風 或私下
講一句「弟兄辛苦了」
很多時候是為了彼此相處愉快
出海(出國)順利一點
船長有時跟他們聊天氣
聊今天看到的海豚
一邊唸著客人怎麼還沒到
一邊悠閒坐著
跟販賣部的小姐開玩笑
也有因規則被刁難的時候
那天碼頭邊除了海浪聲
滿是緘默
公司臨時換一名船長卻開不了船時
他們緘默
船上人頭多了少了
他們緘默
被鏢殺的海豚運回岸上
他們幫忙搬運
然後緘默
人與船在外海翻覆後
他們前去收拾殘局
在船員的傳聞裡
海巡的船有時會在沿岸定點跳曼波
一前一後 一前一後
用原地搖擺的航線
把油錢跟工作交待過去
偶爾 遠方有雨雲撕咬天空
那種日子
出海尋鯨像下注
船長出航前跟柑仔色的大喊:
打雷了,打雷了啦!
語氣像玩笑也像牢騷
那班船裡,船員
全程遠離三樓甲板上的天線
船員在甲板上的雨雲旁站著
像一支避雷針
柑仔色的海巡弟兄在口令裡站著
像一支避雷針
〈現實中的海洋管理〉
1
出港前我們比照遊客
套上救生衣
有人將一兩個扣環扣起
有人只是披著
一離開海巡弟兄的視線
就脫下來
要寫出這件事時
我猶豫兩秒
然後放下心來
哪個崗哨被問到
都可以說
那是其他港口發生的事
2
人民最有感的兩樣東西:
選舉年前馬路上重鋪的柏油
風雨過後岸邊投下的消波塊
海洋生物最有感的是什麼?
可以忽略不計
牠們沒有投票權
3
海洋保護區要設哪裡都可以
別在有魚群的地方就好
4
我們規定了遊艇
和帆船的檢查項目
也在遊憩辦法中提到獨木舟了
只是沒為他們安排
可以下水和靠岸的地方
〈綠蠵龜——記簡船長〉
在每一個漁港
每一艘純白的帆船
都在找可以停靠的地方
船長披上白色外套
像要趕赴舞會
裡頭袒露的胸膛
藏著跟海巡跟水泥堤防
交談磨礪的刻痕
一隻在自己軀殼上刻畫
占卜吉凶的綠蠵龜
不問天氣或風浪
只看港邊的人
他一趟趟跟穿橘色制服的
人們總記不住臉孔的衛兵交談
打趣同時抗議。這些年下來
旁人已讀不出
他在生氣還是在笑
看似揹著笨重的殼
卻來去如煙的綠蠵龜
烈日海風裡無人知曉的
一個渺小的人與另一個渺小的人
之間的外交手腕
在每一次靠岸時展演
有些親切的笑容是堅硬的
有些打死不退的底線隨時準備挪移
像頭纜跟尾纜在一呼一吸間
商量著鬆緊
綠蠵龜*對我說:
你寫出了人間地獄
也沒人要看
但他在靠岸的夜裡
不時給自己滴眼藥水
一雙已經
懶得爭辯的眼睛
一眨一眨,假裝入睡
等待著明天的海
*簡船長的帆船名與綽號
〈給桑迪亞戈
——致恆常不可見的《老人與海》〉
當我漂離中心德目和勵志標語的大陸
才終於在清晨的海濱遇見你
桑迪亞戈
我親愛的老古巴漁夫
你出海四天四夜
從故事中迷航到我身邊
小說未完
消逝在槍聲中的海明威沒有再光顧露臺酒吧
這回你真的是獨自一人了
我也一樣
我們都被迫記住故事主旨
忘掉你的名字
學會寫「不屈不撓」幾個字
而從未涉水航進你的海域
老桑迪亞戈
你雙手的掌紋用割傷鑿成
飢餓和漂流的海風刮走你的機遇
食腐肉的鯊魚分批搶劫你
大船載走你的兒女和孫子去找更多漁獲
你在小船上,被大馬林魚拉向遠方
漂流十五年
來到我定居的東岸
某一天早晨的區間車窗外
船上載著我已幾乎淡忘的父親
這麼多年過去
我認不出他已經成為了你
還是風化成為一條巨魚的骨骸
夢中我也曾駕駛過
這樣一條小船:
老家那由西部搬來的床墊
飄出臥房 在海上降落
童年的風箏線像條不可見的船繩
緊緊繫在我已無從回歸的
家戶欄杆上
然後我順著鋒面南下
來到某間綠皮車廂
和你的小船並肩
老桑迪亞戈
海上只剩下我和你了
你是長者,父親,同伴與對手
是我憂傷頑抗多年
糾纏不去如百來隻鯊魚的命運
我們在大洋上攪拌成漩渦
捕捉海風捲成魚叉,互相戳刺
忘記日夜潮汐正削減彼此的生命
一路搏鬥著
漂向大海的盡頭
在那裡,不會有酒吧
沒有幫忙準備沙丁魚的孩子
在那裡,恩仇和糾纏都將被擱下
只有無從遲疑的消亡
或者倖存
老桑迪亞戈
我親愛的古巴漁夫
這就是你與我如此徒勞
僅僅追尋著巨大骨骸和歸返處所的一生
安睡吧,為了下一次苦澀疼痛的醒轉
為了我們未必能遇見的
深夜裡,非洲獅子群的夢幻
二、遺忘港
〈淤沙——長濱和某些港口〉
這裡不應該有沙
人們不希望有。
淤沙就像是那些東西:
人們希望它堆在自己
每天不會經過的那一側。
所有人的容忍
都在淤積。
無止盡的沙堡遊戲
一個小女孩跑上丘頂
看著游泳的我
我伸腳往下探
水底的沙沒有回答。
流水和巨岩溫柔地
看怪手們工作
鋼鐵的筋肉酸痛
比如快轉的夾娃娃機
比如金魚網盛起一灘汙泥
重量拗彎了手柄
沒有人逃得開這堆沙:
怪手司機 漁會代表
轉動船舵的船長
觀測議題的師生
在沙與港的生產線上
每個人都分到一個位子
去看,而且做。
沙在某處剷除,在另外某處回填。
沙在某處養育獨木舟玩家。
沙被渴望。
沙被拋棄。
沙變成渣滓,變成地基。
一沙一世界,世界們彼此積壓。
沙是最鬆散也最堅實的箴言。
我們終於低頭看見
我們立足在它之上
或者說
在它之中。
〈在旭海,一個上午〉
風浪將礁石
慢慢咀嚼成細沙
鋪出沙灘
我腳下港堤的兩端
將在百年後會合
海裡有答案 沉埋在
我們走不到的地方
再一個小時
我要走到岸邊的海產店
吃炒飯海鮮卷當午餐
傍晚我將得知
它們真實的價格
此刻那輛工程車
慢慢開過來了
一個大叔就要和我攀談
講起這裡忍受飛彈鄰居
換來的修船架
唱出已被大多數人
乃至最後將被他自己遺忘的軍歌
但在這之前
海浪伸手就能摸到的地方
我帶來的洋芋片筒開始滾動
這個還無法稱之「未來」的瞬間
詩集用風翻開某一頁
透過我的嘴 開始唸誦
〈沙洲在看著透視法〉
那漁人將繩子上肩
拖著後頭整個沙洲的塵暴
往逃竄的溪流
往惶惑的海浪走去
和它們會合
等候著的竹筏
被不知什麼拴在岸邊
或者僅僅是 它腳下的那些沙
還沒完全被掏空
在人和船外頭
並不保護著什麼的流水圍繞著他們
或鹹或淡
沖積平原的每一寸
都是入口
也都是逃生門
來去的船隻 無從定居的人們
在觀景窗裡獲贈
一個無所適從的框框
世界悄悄向我透露
規格在它懷中
是如此矮小的字眼
為了拍攝環景
開始轉圈。在擺動的那瞬間
港口、沙洲和岩石
已將一個無故到此的人
圈成全景的一部份
一個無所不有的地方
閃現於自轉中途
螢幕手抖畫成的一格像素裡
在衛星的凝視之中
所有的我們
足以湊成一條朦朧的銀河嗎
〈坡頭少年〉
十五歲,魚腥味養大的少年
在港口風沙與新闢的水泥坡旁
清理舊漁網來賺零用錢
幼稚園開始學釣魚
小四開始理漁網
接繩、觀察網孔
小心理順方向
不要重複打結
他複習這些
等著上船
像那些急切咬餌的仔魚
當他發現我會訪談、拍照
他開始留意鏡頭
像電視上那些受訪的名人
分享著自己才剛展開的生平
他小心把糾纏漁網的
漂流木抽出
然後粗獷地扔到旁邊草地
朝海巡弟兄們主動打招呼
聊天般笑著分享自己的進度
對方只是看他一眼
一把沾漆弄鈍的小刀
路過的陌生環島客
就是他這個下午
全部的朋友了
他說:這個港口出海也蠻常死人的
什麼原因呢?
他歪著頭,看來還沒理清楚
或是已懂得太多
我們在只有三兩個休業小攤
彷彿已被遺棄的漁獲直銷中心前道別。
他說:哥哥
你可以拿這些照片去參賽
會有獎金
真獲獎了他要分多少呢?
這點他始終忘了提
*於新竹坡頭漁港。工程後,風吹起沙堆,棄置路邊。
〈基隆之鷹〉
一隻鷹經過港口和城鎮孿生相連的裂縫
牠從上空滑翔而過
一隻鷹經過山峰上矗立的巨大「K」與「G」
牠從上空滑翔而過
一隻鷹經過鐵支路、霓虹和暗紅的窗
牠從上空滑翔而過
一隻鷹經過砲台、博物館、最近的離島與最遠的水手
牠從上空滑翔而過
一隻鷹經過橋邊的獨立書店和一群彩色的樓房
牠從上空滑翔而過
一隻鷹經過水上城寨、昔日泊滿委託行的街巷
牠從上空滑翔而過
一隻鷹經過天橋和甬道裡或坐或臥割去名字的人
牠從上空滑翔而過
一隻鷹經過紅燈籠、飛檐與沈靜垂釣的神明
牠從上空滑翔而過
一隻鷹經過卡其背心大砲相機久站如欄杆的人們
牠從上空滑翔而過
一隻鷹經過我的朋友和久違到不適合再見的朋友
牠從上空滑翔而過
一隻鷹經過沒有結果有時花都還沒開的愛情故事
牠從上空滑翔而過
一隻鷹經過除了朝婚姻陷落之外無處可去的愛情故事
牠從上空滑翔而過
一隻鷹經過殖民者造船廠軍艦貨櫃商船領海主權界線
牠從上空滑翔而過
一隻鷹經過認同與夢、眼淚與汗、從不入睡的時間
牠從上空滑翔而過
一隻鷹經過親密的雨和陌生的陽光
牠從上空滑翔而過
三、防風林裡的碎浪
〈有時看得見海的列車〉
按下看海的快門
光線後頭便是漫長的隧道
海灘,黏合的山脈
傷疤似的礦場
陸客團與旅遊小家庭
像車窗倒影湧入
席地而坐的人
不必擔心下一站要讓座
行李箱高低對望
每支手機是一顆星星
當隧道席捲而來,黑洞就亮起
天文學家醒了
沒為行李箱設計對話功能
自有原因
有時車窗染上海的顏色
總是回程的人
從另一側隔著椅子張望
一小群親友突如其來的笑聲
是禁不起抽絲剝繭的
車掌慢慢習慣
乘客不帶票上車了
只像要簽帳般遞出悠遊卡
當然這僅限於
最廉價的車廂
我無法把標題定成「海線」
因為在台北跟花蓮間只有一條路
只在悲憤時興建
只在選舉前通車
只在客運廣告裡感謝勞工
只在抗議時安全回家
海被隔在山脈跟隧道後頭
客輪漸漸來得少了
別擔心,拐幾個彎
穿過無從會車的軌道
我們就會來到以完美裝飾的首都
像多年前的電影畫面
不管是向前或倒帶
隧道盡頭必須是光
2019.01.07 刊於鏡文學
〈秋天的開端〉
她附在我耳邊
分享那個我無法承受的秘密
憧憬的五色鳥
被什麼給驚飛了
無法離地的觀景窗裡
樹枝擠出善意
拘謹地招手
我知道
她說謝謝時
沒有——
或假裝沒有在想任何事
我一直都知道
期待濕熱的颱風撲上土地
暴雨淹沒每一個人如同
意料之外的擁抱
窯裡升起的火
悶烤我們無從乾燥的身體
什麼時候
我們已經走過碎浪的界線
看捲浪從眼前蓋下
卻只化身海湧
將我們輕輕托向天空
然後穿過我們 不再回頭
當潮線褪去了腳邊的浪
磕傷我的石頭
都磨成沙灘
就能假裝路過了滄海桑田
守護莊園的狗吠聲
在晚風裡睡著了
它本該辨認誰是朋友
誰是陌生人
我把身體裡的嚎叫
瀉出一點點
她就往後退了
恰如那齣我不願分析
卻總是逕自彩排的劇本
必須用最烈的酒
敬那些從未能演出的戲碼
吹熄所有的燈
讓缺憾而完滿的月光浸透全身
麻雀在園地裡嘰嘰喳喳
沿著機遇留下的足跡 隨意聚散
春天去向不明
不用怕 狗都栓好了
颱風已經一路走到
連海也無法丈量的地方
葉子開始枯黃時
不會特別通知誰
你那顆熱暈的
下水也無法冷卻的心
就用接下來一整年代償
2019.10.28 刊於《鏡文學》
〈某些時間〉
早餐店牆上
那座老是快二十分鐘的鐘
今天回到了此時此刻
我假裝不再恨妒那些人
那些人也順利忘記了我
陽光沒有花時間
回顧昨天的溫度
浪上岸之後
又走回海裡
遇見下一道浪
某個不設定鬧鐘的日子
一個工人扛著
總有一天會把他壓彎的東西
若無其事經過我身邊
他有下一個要去的地方
他還有無數件工作
他沒有趕著要去哪裡
〈翠鳥〉
是你在尋覓河邊的巢
或是我誤認了
天空剝落的一角?
被呵護著的小女孩
雙腳浸了海水
父母將她抱到另一邊
更濁的溪水裡洗淨
幾個從課堂佚失的男孩
垂釣 騎漂流木 脫衣褲
撲進白浪裡 脫胎成魚
釣竿上一串吐司邊
無色的月桃花
在等待與機遇間擺盪
消波塊上
一隻八哥和另一隻八哥討論著一群八哥
直到一團枯葉長出翅膀和腋下白點
朝季風與饑餓
朝厚密如樹蔭的死亡
滑翔 迫降
攀住垂落的陽光
萬花筒的圖案轉瞬即逝
民眾提著鳥籠逡巡
獵人在童話的續集裡迷路
幸福不是有翅膀之物
沒有嘴喙
或靈動的眼
只是翠鳥回巢途中
恍惚偶然的一瞥